钟馨回忆录之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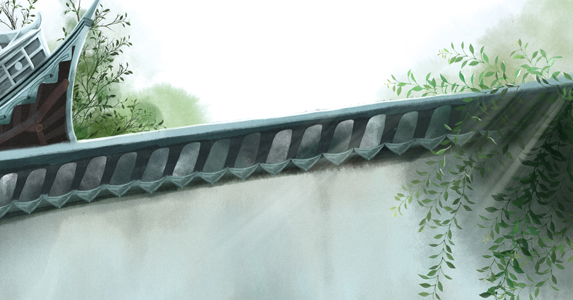
人生在世,不知会遇见多少人,发生多少事,经历几多生死,斯人,斯事,难言悲喜,皆不可追,奈何知之已晚矣。
而今,韶华远去,斯人已逝,我亦年老体衰,心力皆乏,所能做唯有以笔下拙文恬为祭矣。
——钟馨
1978年于北戴河疗养院
1
惊蛰一过,春暖,风和。
头上的天,却乌云压顶。
河南的饥荒愈演愈烈,北平里流民愈多,坐在金家那花草繁盛的花园里,仿佛都能闻到饿殍的尸臭气。
匣子里的广播更是听得人心口发堵,日本入侵了缅甸,日本向荷兰宣战,泰国又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德国纳粹宣称要杀光犹太人……
“这世界,打圈儿仗呢?”婆婆守着匣子呢喃。
自从四妹茹英来信说去了广州做军区医生,婆婆便每天坐那等着听前线的战事,闻得赢了长舒口气,闻得输了便久跪佛前。
战争带来的灾难无法转述,活着的受尽屈辱,死去的无处安息。
金家的处境也日益艰难,东四的宅子被分成两家租了出去,东院的租户是位姑娘。
她很年轻,二十出头,和一位年轻先生一起租下了院子,那时她还大着肚子,可没多久,那位先生就搬了出去,她在这院子里生下孩子,又送走了孩子,至今已六个多月。
我偶尔会替大嫂去收租,她总是很安静,把钱放在纸包里递给我,客客气气送我出门。
她的窗前种着许多盆茉莉,因着窗台下就是火炉,熏得茉莉早早就开了花,单瓣的白色茉莉,香得人不忍离去。
上一次大嫂回来说,遇见了一位矮个的先生,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也很响亮,两人很是亲近。
今儿我又去了那宅子。
她刚刚从邮局回来,心情很是不错,见到我忙问:“三少奶奶来了,可是月租提前了?”
“没、没,怎么会呢,有人来瞧西院的房子,刚送了走,顺便来你这转转。”我连忙摇头。
“哦,屋里请吧。”她松了口气。
“买书去了?”我看着她手里的书问。
“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她笑着递了过来。
“原来乔吟小姐是位作家啊。”我接过杂志赞叹道。
“没、就是……写着赚点稿费糊口的……”她一边应声一边拆着手里的信。
“啊,三少奶奶,有件事想麻烦您,听说您留过洋,我这有封信想请您帮忙翻译一下。”她不好意思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
“哦,是上海的一家女性英文杂志,很欣赏您的故事,希望能收到您的稿件……”我把信件递还过去。
“三少奶奶的英文真好,乔吟自小家里穷,勉强上得几年学认识几个字,比不得您这般有学识的……”乔吟不无羡慕地叹了口气。
“您客气,作家可不是只识得几个字就成的,太谦虚了。”我连忙寒暄。
“穷够了,就总盼着能出人头地,拼了命地读书,也才混个温饱……”她拿起那信封自嘲地笑了笑,信封里掉下一张汇票,当是这次的稿费,她忙蹲下捡起,收得小心翼翼。
“东西我给你拿回来了。”院子里忽地进来一人,高声说着什么,瞧见我愣了一下,让过一旁,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就又冲乔吟笑道:“他不给我,我就把刀子拿出来,还没怎么着呢,他就怂了,哈哈哈,这个孬种……”声音洪亮,个子不高,邀功一般提着个布包。
“咳咳,这是房东,三少奶奶……这是我……”乔吟有些尴尬,略略迟疑间,那男人就接过了话头。
“我是他男人,我叫李军。”他介绍得倒是痛快,想来是个性格爽快的汉子。
乔吟笑了笑,接过李军手里的包裹,对我叹口气道:“这裘袄是他走时候带走的,总是不肯还我,世道不好,讨回来换几斤米面也好……”
那的确是件不错的袄子,皮毛油亮,样式洋气,可比几斤米面值钱得多,而那个他,自然是早先的那位年轻先生。
“说那干啥。”李军的脸色不大好看。
乔吟抿了抿嘴唇,没有言语。
“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做去,三少奶奶一起,我老李家的酸汤子(一种面食)那是全城都出名的,你今儿算赶上了。”他说着就往厨房去,我连忙推脱,客气几句赶紧走了。
出得门来,长舒口气,这汉子人倒是好人,只是脾气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乔吟与他,就像海棠花枝下埋了颗番薯,不搭。
2
不过两三日,院子里的丁香就开了满树,香气跋扈本不讨喜,可这样哀颓的日子里,这香倒是驱去不少战争的硫磺气。
乔吟坐在那树下,阳光散在枝头,树叶间的光斑投射在她身上,越发显得整个人柔润似水。
今儿一大早她便来金家寻我,央我替她翻译文稿。
我拿着她的稿子细细地看,她坐在那,面前的茶杯一动未动,很是紧张。
“我识得一位专业做翻译的……”我放下稿子迟疑道。
“三少奶奶,您帮帮忙,翻译的费用虽然需得晚些给您,但我一定会付的,请您帮帮忙吧,我也实在不知道有谁的英文比您还好了……”她站起身急切地看着我,一双杏眼闪着诚挚的光。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是您写得太好,我怕愧了这好文笔。”我连忙解释。
“三少奶奶客气,乔吟就拜托您了,何况我也实在付不出太多的费用……”乔吟低下头,又抬头冲我笑了笑道:“不过也许以后就好了呢,说不定我写完这些稿子就出名了,到时候,只怕更要麻烦三少奶奶了。”
她的笑容也是柔和的,高兴也好,急切也罢,她都是柔和的,她就像一团棉花、一片云朵、一觞流水,没有棱角没有脾气。
送走了乔吟,我仍回那树下,她坐过的地方已落了一只菜粉蝶,茶杯里的水仍如初。
“……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坚定地相信我们是对的,直到结局把我们摔打进泥里,然即便得了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仍还是会这样想,这样做,这样被摔打进泥里。如此,才是你我,不可救药又无能为力的你我……”
这是乔吟的文字。
乔吟的笔是凉薄的,也是坚定的,和她的整个人,也是不搭的。
转眼处,瞧见一纸汇票落在长廊下,想来是乔吟起身时掉落的,匆匆忙追出去,她已走到了胡同口,好容易在电车站前才追上了她。
正待近前,却瞧见李军从车站前的灯柱下站起身来,迎上乔吟,一把拉住高声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去哪了?”
他站起身也只比乔吟高一点点,人长得黑而壮实,额头已晒得泛了油光,不知在那灯柱下蹲了多久。
“没去哪,和三少奶奶聊了几句。”乔吟答得轻,她低着头,让人看不见表情。
“乔小姐……”我连忙赶上,递过汇票道:“您的东西落下了。”
“哎呀,瞧我这个迷糊,多谢您了,不然一会儿到银行可是要急了。”乔吟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
“收好收好,世道不太平,小心些好,这可是您的劳动成果呢。”我客气几句就要走,却听李军笑道:“嗨,什么劳动成果啊,也没几个钱,这不有我呢吗,不怕,你这个稿子日后写不写的也不打紧,我看就不写了罢,我养你……”
他热切地挽住乔吟的手,他是喜悦的,也是炫耀的。
“不,我要写。”乔吟的声音少见的尖锐,看着李军的眼神坚定而郑重,这眼神像一支冰箭,穿透李军洪亮的嗓音,把他的喜悦和炫耀都冻了住。
“你……”李军皱着眉,扭头瞧瞧我叹了口气:“得得,写吧,写着玩也好,总比那些娘们打牌看戏强得多,走吧,我薪水下来了,给你买身新衣裳去……”李军说着拉了把乔吟。
乔吟跟着李军走了,娇小的身子依偎在李军身旁,仍是那么柔和的模样。
重回院子里的丁香树下,方才的茶水已被家人收了去,菜粉蝶也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跋扈的香气,氤氲不散,捏着乔吟的稿子,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3
因着译稿的事,我与乔吟的走动多了起来。
李军不喜乔吟外出,所以大都是我往东四的宅子去。
这一日,仍是我去送稿子,进门的时候,乔吟正在给窗下的茉莉浇水。
“你这花养得真好,一年倒要开上三四次。”我笑道。
“以后大概不会开那么多了”乔吟叹了口气道:“炭太贵了,不大冷的时候就不燃了,这花儿只能应季开了。”
“反正花总是要开的,晚一些说不定更香呢。”我应道,她说的没错,不光是炭,什么都贵了许多,连豆腐都要七角钱一块儿了,去年还只要一角五分。
“哎呀。”她浇水的喷壶突然掉了下去,正砸在花枝上。
“这怎么浇个花还……”我正要打趣,却瞧见她胳膊上一大片青紫。
“这怎么了?”我替她捡起喷壶问道。
“没、没怎么,这不想着把炭盆收起来,没想到自己这么没用,出门时候撞门框上了,这会儿连个喷壶都拿不动了。”
她扯下袖子遮住伤口,柔柔地笑着与我聊起稿子的事来。那家上海的英文杂志很是中意她的文字,想请她做个长篇的连载,稿酬也是提了许多,她很兴奋。
第二日我自婆婆那取了些赤芍红花这些活血化瘀的药,给乔吟送去。
遇见西院的租户便聊了两句,老人家说的陕北话很好听,和秦腔一般的硬气,不见那袅袅悄悄的音和调,一句是一句地砸在地上,想不认真听都不行。
这一聊就聊了一个多钟头,待得我往东院去的时候,太阳已快当头了。
“你就不能听我话吗?你怎么就不听话?你能不能听话?”李军的声音传出来,比平时更高声,更暴躁。
“啊……”乔吟的喊声,接着就听得“咔嚓”一声响,是陶瓷器碎裂的声音。
我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不礼貌,慌张张冲进去。
李军正把乔吟从地上拉起来,一盆茉莉碎了,粗陶的花盆裂成四瓣,泥土散了一地,花根从土里露出来,和被压出汁液的枝条躺在一起……
“这是怎么了?”我上前要扶起乔吟。
“没、没站住,没事。”乔吟连连摇头轻轻推开了我。
“啪!”李军突然扇了自己一巴掌。
“我劲儿大了,下手重了,我不是故意的,吟子你别怪我,我真不是故意的,都是让你气急了……”他突然看着我说:“三少奶奶,您做个见证,我李军以后再动吟子一根手指,我都自断双臂……”
“胡说什么呢?把东西收一收吧,来人了,怪难看的。”乔吟打断了李军,她的话还是那样轻柔,可她的眼睛看着地上,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李军。
“他……为什么?”看着李军出去,我悄声问。
“我昨儿出去了一趟,他惦记我,怕我出意外……他就这样,脾气急了就管不住自己,平日不这样的,没事儿,今儿就不留三少奶奶久坐了,家里乱……”乔吟看着我笑得温和,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似的。
回去的路上,我仍是想不明白,难道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想起昨日,直到我走她都再没松开过扯下袖子的手。胡思乱想地走回家,碰见恒英下班回来,冲我笑:“这怎么送药的人,又把药拿回来了?”
“哎呀,忘了!”他说我才发现,这药又让我拎回来了。
“恒英,你说,为什么清清明明的一个人儿,有时候会做让人看不清明的事呢?”我问他。
“大概是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太多,清明不了了吧。”他说得自然,我却陷入沉思。
4
天灾难测,政府已拨了款,又把附近省市的粮食运去了河南陕北赈灾,灾情已得到了控制。这是匣子里的官话。
从河南逃亡陕北的路上,是走不了车的,因为路都被饿死的尸体铺满了。这是东四宅子里那说陕北话的老人家说的。
“粮食又涨价了,早间还三块二一斤呢,这会儿就四块三了。”这是外出采买的家人说的。
北平的粮价一日要涨三次,其他的物价也是水涨船高,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能值套四合院了。
金家的进项不少,可自从公公失了实权,其他人的仕途也就一并走了下坡路,凭着这些薪资是不可能撑住金家这偌大的产业的。
老爷子到底还是开了家祠后面的库房,他站在祠堂前看着二哥和恒英把那两个半人高的银胎珐琅彩嵌八宝梅瓶搬上车,脸色阴沉得像攒了一冬未下雪的天,昏暗,可怕。
瓶子被悄悄送去了二哥的古董铺子,谎称天津卫贵人家的货出了手,此后谁也没提过金家曾有过这么一对八十斤八两的银瓶子。
金家尚且如此,更遑乎普通人家。
乔吟早已搬出了东四的宅子,另租了户偏僻的小院儿落了脚。
她与李军照旧住在一起,每日里精心伺候着那几盆茉莉,身上还是时常带着伤,虽已熟识,却总是客客气气,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来往着。
恒英年前便受聘往北师大任教去了,近期校里成立了一个英语协会,我因着恒英的关系得以任了个辅导顾问的名头,也是越发的忙,与乔吟的联系也就更加的不咸不淡了。
待得东四宅子的新租户搬进来时,我才想起乔吟上一次托我译的稿子还未拿回去,已两月有余。
乔吟的新家是不通电车的,我拐过胡同口的时候,早先的那家馄饨摊子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乞者歪躺在一起,胡子留了满脸,瞧不出年纪。
“你走?你走你就得饿死,你走一个我瞧瞧,我打不折你腿……”还没到院门,就听见李军的大嗓门叫骂着。
我站在门口,有些犹疑:“既然管过一次,未得人家待见,又何必再多事呢?算了,回吧,人家两口子也不是第一次打架了……”我暗自思忖。
伴着院里什么东西“当啷”落地的响声,我慢慢向后撤了一步正待转身,却听得里间撕心裂肺大喊:“啊呀,你个疯娘们,草,血,杀人了,救命啊,这女人疯了……”
“砰”,院门被猛地撞了开,李军冲了出来,半个膀子殷红一片。
李军的喊声引来了路人和邻居,他捂着胳膊在门口高声叫骂:“你个疯婆娘,我养你吃养你穿,我替你做了多少事,你砍我?你他娘的你丧良心个婊子,老子对你比对我娘都好,你砍我,你个白眼狼……你、你……”
他骂着骂着突然带了哭腔:“你至于吗你,老子不就让你在家养养身体,别出门吗?你至于吗?我对你哪不好?哪不好?”他哭得越发大声。
“自从跟了我,你一天厨房没下过,一天冻没挨着,老子哪不好?老子他娘的哪配不上你?你以为你黄花姑娘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可你他娘的凭啥看不起老子?
老子正经人,靠本事赚钱养你,你个让别人赶出门还生过野种的婊子,老子赚钱养你,你还……他娘的敢还手,老子打不死你……”李军的哭又转成了叫骂。
乔吟就那么站在门口听着,手里提着一把镰刀,直直地看着李军站在大街上叫骂,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一动不动,像一尊结了冰的门神,又冷,又狠。
李军骂累了,刚要抬脚往回走,乔吟却举起镰刀冲了出去,没有预兆地狠命向李军身上砍。
“滚!”乔吟喊得竭力,只一声,已破了音。
通红的双眼,带着血的镰刀,散乱的长发,没有人敢再靠近,看热闹不是管闲事,热闹大劲儿了,就没人看了,众人纷纷躲避,生怕那镰刀一不小心搂在自己身上,而李军更是一溜烟跑得无了踪影。
5
刚刚还喊打喊杀的胡同,转眼就只剩下墙后的几双眼睛。
我战兢地躲在门板后,不知该如何。
乔吟犹自站在街面上,任凭秋风吹过,散乱的长发胡乱飘舞,一枚黄叶打着卷地从树上飞下来,这已是那棵树的最后一枚叶,冬要来了。
叶还未落下,乔吟瘦弱的身子突然跪倒了下去,像一根折断的枯枝,手里的镰刀犹自握着。
“咳咳……”我轻轻咳嗽了两声。
乔吟回过头,看见我,通红的眼里突然滚出了两行泪,镰刀“呛啷”一声落了地。
“你这……我给你倒杯水吧。”我把她扶进屋里,想问,终还是改了口。
“死了,她死了,他骗我,骗我……”乔吟抓着我的手腕,眼泪像开了闸的水流,话不成声。
我任凭她哭,直等得眼泪流完了,才悄声轻问:“谁?谁死了?”
她抽噎了几声,看着我,眼底一抹的黑,泪水淹没了所有的光亮。
“我是个傻子,三少奶奶,我是个傻子……孩子死了,李军说把她送到了一户没有孩子的好人家……他骗我,他把孩子卖了,孩子没满月就死了。上个月他不在家,那个抱走孩子的人来寻他讹钱,口口声声说孩子先天不足才没的,让李军退她钱……
这都快九个月了……骨肉都烂了吧……连名字都没给她取一个,就没了……”她缓慢地说着,一字一句地说,偶尔停顿抽泣一阵,再接着说,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
“如果不是遇见我,李军大概算得个好人,瞧着我一个人可怜时常来帮忙……替我请大夫接生,给我熬粥坐月子……”乔吟说了几句,自嘲地摇了摇头,“哪有什么好人坏人啊,还是我自己不争气罢……”
李军劝乔吟送走孩子,乔吟无依无靠,身体虚弱,又沉浸在上一段情感的伤痛里,便应了,可孩子送走以后,无论乔吟怎么问,李军都不允她去看,问得急了,便会吵,吵得急了,便要挨打。
“后来我就不问了,他宝贝我,我总归能查出孩子到底送去了哪,就这么的,我挨过了这些时候,我也想过,如果一切都好,那就这么过吧,他是个好人,只是……”她说到这,突然笑了,“三少奶奶,您定要觉得我矫情,是的,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我,配不上。”
乔吟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摇摇头道:“三少奶奶,您回吧,我自己的事,还得我自己来,他再伤不了我了,以前我是由着他打,现在不了,我犯不着了,你回吧,我也走。”
“走去哪儿?”我瞧着她搬下箱子,开始收拾衣衫,毅然决然的模样竟让我有些想要流泪,却说不出是欣慰还是悲伤。
“哪儿都行,走得远远的,我留在这也就是为着有一天能再见着孩子,既然见不着了,哪都一样,咱们也后会有期吧,三少奶奶。”乔吟只装了两件衣裳,一沓文稿和一条小婴孩的抱被,她的行李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她已无甚也无需再带更多。
“总要有地儿落脚吧。”我跟着她往外走。
她没有应我,拢了拢头发,冲我挥了挥手,她的眼睛还肿着,衣裳上也染着血,但她走得很快,脚步急切,不再回头。
6
人想杀人,是很难的,一个人再凶狠,也不过杀去百十人。
天想杀人,却很快,一两年,尸体漫道,白骨嶙峋。
1943年的夏天,饥荒勉强算是过了,至少匣子开始说河南米粮的收成了,到底死了多少人,空了多少房,却没人再提起,就像金家那对银瓶。
天灾过了,人祸还在,战争愈演愈烈,国内国际皆是如此,大哥家的长子冠均突然失了音信,老爷子不允人问起,对外只说送去留学,实际上是因着党派之事,怕遭伪政府查处,不得不逃了。
金家有很多对银瓶,曾经存在,又被抹去了痕迹,可笑,可悲,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金家还有更多的金罐子,明晃晃摆在那,生怕人看不见。
大夫人做寿,排排场场的流水席,又是拜佛,又是施粥,帽儿胡同人声鼎沸。
今日请了同春班的陈大春来给大夫人唱戏祝寿,淡儿姐早早就嚷着要去后台瞧。淡儿姐已十岁,受着她二伯父的熏陶,整日地抱着匣子听京戏,不时地嚷着要拜师学艺。
这陈大春前不久才在大栅栏的三庆园唱了几场,外地来的班子,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我和大嫂带着淡儿姐去凑过热闹,唱得也不过尚可罢了。
戏要午饭后才能开锣,班子里的人这会儿正在厢房里提前用饭。
“陈大(de)爷可在啊?”家人前去叫门,我们站在院子里再一次嘱咐淡儿姐不允乱讲话。
“陈大爷后面扮着呢,您稍等一……”应声的是个女子。
“乔吟?”我惊呼,她站在门里,笑得柔和。
整整一个午后,我都与她坐在廊下。
她的故事并不大长,那日分别后,她无处可去,在市郊的大车店住了几晚,便去了投过稿子的杂志社,想问问此前的稿子可发了,能否预支稿费,恰巧遇到陈大春来登广告。
“那时他也才来北平不久,班子还没立住脚,我与他聊了一会儿,也算投缘,后来又见了几次……”她顿了顿,偷看了我一眼,又继续道:“几次之后,我便随他一起去了园子,帮着洗洗衣服晒晒行头……”
乔吟说得轻巧,却看着地面讽刺地“呵”了一声,抬头看向我:“三少奶奶,您可是轻看我了?我也是没得办法……”她讲得简单,可简单的事也许付出的代价更大,只是不可与人言罢了。
“哪里的话……看年景,死一村人和死一个人一样容易,谁不想活着呢?再说,能遇见合适的,也是缘分……”我叹了口气,这个世道,怎么活都是好的。
“向前看容易,向前走……哎……”乔吟脸上的无奈即尴尬又卑微,与那个甩着头发拖着箱子离去的身影再合不到一起。
我们就这么坐着,没有再会的欣喜,也没有拜别的离情,更没人提起更多过往,只等得戏要开锣,才各自忙去。
7
这一年的秋天,伴着匣子里高高低低的广播声,如时地来了。
可匣子里的广播却好像永远播不完,缅甸独立了,意大利投降了,反奸政策刊登了,重庆大轰炸结束了……
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没有人知道今天的步子迈得对还是错,没有人明白这个国家的旗帜到底会指向哪里。
“学校这几日怎这样忙?”我问恒英,他几乎日日晚归。
“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大家都热情高涨,自然要忙一些。”他坐在饭桌前,面色疲累。
“你终于也要站队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
“什么队不队的,站哪边不都是这一片土地嘛,事情只看对错,然对错这种事,也不是一时能判定得了的。”恒英盛了一碗汤放在婆婆面前。
“那怎么判定啊?”淡儿姐一脸茫然。
恒英笑了,却扭头去问憬一:“儿子,你说呢?”
憬一眨眨眼,蹙着眉头认真道:“那就不判定吧,反正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的评说不都是留给后人的吗?”说罢,又接着吃起那刚刚咬了一半的什锦丸子。
“胡说,什么都留给后人,现在还活个什么意思?我这会儿才吃了四个丸子,要是留给后人,那我这丸子是不是就不能再多吃了?那我不就饿死馋死了?那我还哪来的后人?”
淡儿姐已到了会胡搅蛮缠的年纪,时不时就要找着话题和哥哥辩上一辩,但憬一大都是不理她的,一如现在,他也不过是夹了个丸子放进淡儿姐碗里,不再理她。
“要从宏观上看……哥哥说的……”恒英刚刚开口,淡儿姐又接过了话头。
“什么观不观,有什么关系?反正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和对错你不都是要留给后人评说的吗?”淡儿姐嬉笑着晃了晃脑袋,两个小辫子拨浪鼓一样甩起来,好不得意。
“你这……抬杠!”恒英无奈地看向我,我自是不应声的,他们父子间的热闹最是好看。
待得这顿热闹闹的饭结束,我才趁着煮茶的工夫又问恒英:“你觉得哪边是对的?”
“民主,无论哪边说再多的话,做再多的事,只要偏离了这一个宗旨,就是错的,我判定不了未来,只能可着眼下了,哪个为人民解放,哪个为当官的自己,总还是能看出来的。”恒英转了转茶杯,低声道。
我没有再问,安心煮我的茶,金家的人不算多,但大都处在庙堂,庙堂太高,容易让人忽略对错,幸得,恒英做了对的选择。
“三少爷,有客访……”我的茶还未喝到嘴,就有家人递了名帖来。
恒英有些诧异,一是这时候递帖子的人已不多,二是这个时辰还来访未免太晚了些,打开帖子来是烫金的三个字:“陈大春”。
忙请了入内宅,只见陈大春一身的断面长衫,乔吟随在一旁,笑得柔和。
“早就听闻金恒先生大名,这会儿才来拜会,见谅见谅。”陈大春进屋就是一礼,话说得客气,人笑得可亲。
“哪里哪里,陈先生客气,金某一介书生谈何大名,早前母亲大寿,陈先生甚好,果真名家。”恒英回礼,人到中年自然圆滑许多,早年间他是不会这样说话的。
“是大春冒昧,这么晚才来,只怪乔吟今儿吃饭时候才说,原来早与三少奶奶熟识,如此大春才敢唐突如此。”陈大春笑呵呵地看了一眼乔吟。
不知他来此为着何事,又不好开口直问,只得四个人你来我往地说着恭维话。
“乔吟的文章很是不错,当得起才女的称号了,不知现在可还写?”我没话找话地问。
“写,一直写的,大春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帮了不少的忙。”乔吟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是是,我也一直是鼓励她写的,日后我也好跟着沾沾才女的光嘛。”陈大春顺势打趣,乔吟笑得羞涩。
“说起来,我今日正是为着文坛的事来的。下周末在和平路饭店举办文艺与和平的座谈会,国民政府的陈公也要来做演讲,金先生在哲学界的地位,自然要在邀请之列,据说此前已发了邀请函,只是一直未得金先生回应,故而大春今日才再次冒昧前来……”
陈大春笑着说完这一番话,只看着恒英如何表态。
“国民政府?南京的还是重庆的?”我先开了口。
“自然是南京的。”他笑了笑,有些得意。
“是了,您刚说陈公,自然是南京的。”我应着起身翻看黄历。
南京汪伪政府一直自称国民政府,想不到陈大春竟然是他们的人,无论是恒英决意站在共产党一队,还是国民党一队,都必然不会是汪伪政府这一队。
早前的邀请函的确是收到过的,学校收到了,家里也收到了。师大的老师或者公然加入党派,或者年岁太大身体不便,恒英便成了他们极力争取的最佳人选,但每一次都以课时安排紧张为由谢绝了,想不到这一次竟请了说客来。
“陈先生太客气,金某刚过而立,谈何哲学界领军人物,不过一介书生罢了。”恒英对去与不去,避而不谈。
“金先生自谦了,大春自外省来此,能立住脚把班子撑起来,还是陈公帮的忙。这一次陈公为座谈会一事忧心,大春得知乔吟与三少奶奶熟识,便想做个说客,还望金先生拨冗出席,一同为国事尽一份力,何如啊?”陈大春言辞恳切,说得竟有些激动。
“说起来,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我打断了他的激动。
“啊,我们……不忙,不忙,先立业,先立业。”陈大春连连应声,乔吟坐在他身旁,不动不说,偶尔笑笑。
一时间,屋里没了声音,越发衬得方才的热闹虚假。
“金先生……”陈大春想再开口,再一次被打了断,是乔吟。
“太晚了,叨扰三少爷三少奶奶了,我们回去了,改日再见吧。”乔吟率先站起身,也不管陈大春如何,已向外迈了步子。
送走了陈大春,我和恒英站在门口,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你为何叹气?”我问恒英。
“给我盖个高帽子,我一去就会换个说法,眨眼就会变成是学校出面支持汪伪政府……想想都可怕呐。”恒英又叹了口气。他说的没错,自西南联大成立在昆明以来,北师大已然是北平高校的代表,这个时候,太敏感了。
“你又为何叹气?”恒英扭头问我。
“为了乔吟……她走得太远,自己都抓不住自己了……”我晃晃脑袋,扯着恒英的手往屋里走,他的手又温热又厚实,如早年间一模一样。
8
恒英没有去参加那个座谈会,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是否又遇到了什么,但他确实比以往更加的忙,他的论文写了一篇又一篇,刊登在校刊和报纸上,来投帖子的人越发的多。
公公和大哥都很高兴,可恒英只觉得好笑,他常说,那些来投帖子的人里也许连他的文章都还没看过,那些看过他文章的人里,也许只有一两个真的看懂了,每每有此感叹,淡儿姐便来胡搅蛮缠一番,笑闹作罢。
日子就这样过,恒英忙,我也忙,为了翻译《吉尔布拉斯》一书,我在做大量的功课,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要成为一个诗人或者流浪者,但战争不允我有这样的妄想,如此年景下,没人能做流浪者,他们都死了。
新的一年没有任何悬念地越过越糟,金家的银瓶已当了不知多少对儿,东四的宅子也不知换了多少户,街口的乞儿冻死了不知多少个,旧的去了,新的自会再来。人成了没有记忆的石子,能活着比什么都强。
日本人的横行终于受到了阻击,新四军攻克了淮安东桥镇,这个小小的胜仗,已足以让人兴奋许久,连淡儿姐都唱了一整天的儿歌,她还小,但已明白了什么是战争。
我给婆婆换了个新的匣子,更小,更清楚,她越发地守着那匣子不动地方,夏天靠在榻上听,冬天盖着毯子听,春秋带出去长廊上听。
日军诱降的广播刚完,延安就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重庆重拳出击之后,汪伪又征新税,老蒋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不久,一号战役就死了几十万人……
一条一条的广播,死去的人成了数字,随意地蹦,随意地长,听得老太太几乎睡了去。突然,汪精卫病逝的号子大声地喊起来,老太太睁开眼听了一会儿,又闭上了眼,这一听,就又是一年。
陈大春的班子名声无两,他已不大登台,反倒成了北平文艺协会的名誉顾问,不时地上上小报,颇有些政务繁忙的意思;乔吟的文章也发了几多,成了名副其实的才女,只是两人再未来过金家。
1945年是个不错的年头,虽然物价还是一样的高,死去的人数还是一样地增长,终于在春天来的时候,日军在国际战场接连败退的消息,给中国的天空填了一抹暖意。
据说日军大部都奔赴南方战场,虽然不知真假,但北平的大街上似乎当真宽敞了不少,巡逻的大兵不再多得那么碍眼了。单是这条不知真假的消息,已足够让人雀跃。
学生们印了许多“日本即将战败”的传单,趁夜散发各处,一时间人心大动,没多久全国都喊起了这样的号子,一张传单,几个字,成了燎原之火。伪政府发了疯一样四处辟谣捕人,学生代表接连被拘禁,每天都有杀人的布告贴出来,可这火却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样的春天里,我收到了陈大春和乔吟结婚的邀请。
他们的婚礼很新派,也很热闹。早半个月报纸上就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和新婚的喜帖,整整半个篇幅,十分显眼,以至孩子们也吵着要去。
北平最大的西餐厅,红色的地毯四周摆满了各色的绢花,金色的绸面椅套,高大的吊灯足有三四米长,宾客皆是时下的名人和政客。乔吟穿着大红的旗袍,整张脸被头饰上的金凤映得娇媚如花,站在舞台正中央,挽着陈大春笑得柔和。
陈大春的致谢词很长,从感谢宾朋到政府决策,从自幼受苦到当下成就,淡儿姐和憬一听得直打哈欠,好容易共饮了喜酒,两个孩子便直奔餐台,驻足在那些奇形怪状的蛋糕点心前,他们还是第一次参加西式婚礼,又新奇又拘谨。
我看顾着他们生怕失礼,乔吟又一直忙碌,直到离去前才得以匆匆说了声“恭喜”,她看了我半晌也只是笑着道了声谢,她的眼角已有了细纹。
一出餐厅的门就像结束了一场华丽的梦,晃眼的阳光下跪伏着四五个乞儿,晒得黝黑,瘦得嶙峋,有的还带着伤,伤口上的苍蝇和他们的人一样疲怠,人来人往,不为所动,说是乞儿,不若说是等死的牲口更为贴切。
灰黑的地面上偶尔被风带过一角撕碎的传单或海报,踩到的人像踩进了开水盆一样慌忙跳开,疾步绕过,日本大兵巡逻过来时,连孩子都站立墙边低头禁声,不时传过日兵拗口的中文斥骂……
我想叹息,已懒怠叹息。
孩子还沉浸在方才的气氛里,争论着哪个太太最好看,哪种点心最好吃。
“最好看的不该是新娘子吗?”我加入了他们。
“不,妈妈,那新娘子不好看,她笑得假。”憬一回答得直白。
“就像一幅画,没大意思的。”淡儿姐摇着脑袋附和。
就像一幅画,我默默重复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活得像幅画的呢?
9
槐花开了,又落。
星星之火起了,又熄。
槐花还会再开,星火总会燎原。
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距离我最后一次收到东北的家信已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表哥一家生死无音;而金家祠堂后的库房则已空了大半,大夫人偷偷把自己的体己钱都给了二哥,让他想办法出国,二哥不肯收也不肯走,来与恒英叹息着絮叨了一夜。
公公彻底退了下来,他老了,也病了;大哥与大嫂撑着家业,三个孩子已长大成人,可当下留在身边的只三子冠勋一人;我和恒英终日在学校里忙碌,婆婆看顾着孩子们,不肯迈出金家一步,她惧怕外面的世界,听匣子成了她唯一的娱乐。
“德国什么绿翠的啊,灭了,投降了。”她跑来告诉我,转又问我:“日本什么时候灭啊?也快了吧?”不等我回话,她已摇着头走了,她并不需要答案。
但她的答案竟很快就来了。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
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
街头的欢呼声坐在西院的廊下都听得清楚,学生们挨家挨户地拍打门窗,宣告着如此消息。
漫天飞舞的海报,熙熙攘攘的人群,哭笑声和口号声一样震耳欲聋,孩子们捏着传单冲进人群,婆婆在淡儿姐的招呼声中,多年来第一次迈出金家那枣红色的广亮大门……
这喜悦持续了好多天,孩子们每日都要上街去看日本人撤军的车又开走了几辆,那些过往交好的日本朋友也大都随军离去了,他们向往和平,才学出众,但战争隔绝了一切包容心。还有一些中国人顺势走了,逃得远远的,他们走得安静而迅速,背负着汉奸的罪名。
乔吟尸体待领的消息发在报纸最边缘的地方,距离她的婚礼不过四个月。
陈大春就是那些安静而迅速逃走的中国人之一,汉奸的罪名落在了乔吟的头上,她和其他许多汉奸家属们被重庆政府派来的专员带了走,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报纸上只说是病亡,然她哪里来的如此急病?
我拿着报纸寻去停尸的地方,却不敢进,消毒水的味道从紧闭的大门里挤出来,蹿进鼻子激得人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守卫的警察打量着每一个停在门口的人,我终还是没出息地走了。
欢庆日本投降的游行和各种活动持续了好几日,彩旗海报满街地飞,连茶馆里说评书的都改了一段儿又一段儿日本投降的笑料来讲,天桥上捏面人儿的更是把孙悟空和关二爷都改成了提枪打日本兵的模样,孩子们一个个赶着去瞧……
乔吟的尸首,则一直无人认领,我联系过那些曾求着她刊登小说的杂志社,也不过一句“无能为力”。我也曾试图去寻过李军和最初伴着她一起来租房子的青年先生,然也俱是杳无音信罢了。
乔吟的尸体和其他被冠以各种罪名的人们一起被送去了乱葬岗,也许有张草席裹着,也许什么都没有,更也许是和很多尸体混在一起,任着谁的胳膊压着谁的头,谁的左脚踩着谁的胸骨,屈辱地埋葬在谁也辨不清谁的大土坑里。
他们自是不愿的,可他们也已无能为力了。
乔吟更是不愿的,她一直都想好好活着,一直努力想办法活着,一直为了活着而委屈着,终还是落了个“无能为力”的结果。算起来,这一年,她才31岁……